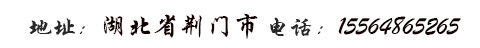金灿荣你可以不喜欢美国但你必须理解美国
|
白癜风治疗要花多少钱 http://m.39.net/pf/a_4629682.html 金灿荣:你可以不喜欢美国但你必须理解美国 人物周刊: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?比尔德和玛丽?比尔德夫妇有一部书《美国文明的兴起》,美国的历史那么短,可以算一种文明吗? 1金灿荣:美国是一种现代文明。美国文明的主体从欧洲来,属于欧洲盎格鲁-撒克逊这一支。我们常常把欧洲视为整体,实际上欧洲的情况非常复杂。欧洲文明至少可以分三大支九小支。三大支就是北欧、南欧、东欧。每个大支都有三小支。盎格鲁-撒克逊是北欧文明中的海洋分支;日耳曼文明,也叫条顿文明,是北欧文明中的大陆分支;还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文明。现在世界上比较风光的实际上主要是北欧这一支。我们说现代化主要有几种模式:德国模式、英美模式、瑞典模式,都在北欧。 南欧也是三支,一是高卢,就是法国;一是伊比利亚半岛,西班牙和葡萄牙;还有一支爱琴海文明就是意大利和希腊,马其顿也可以算一点。 东欧就是西斯拉夫、东斯拉夫、南斯拉夫。西斯拉夫包括波兰、捷克、斯洛伐克;东斯拉夫包括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,乌克兰西部一小部分也属于西斯拉夫;南斯拉夫包括塞尔维亚、斯洛文尼亚、克罗地亚、黑山等等。历史上保加利亚也算在南斯拉夫,但他独立以后说我是独立的一支,跟南斯拉夫没关系。总之欧洲很复杂,除了这三大支九小支,还有几个搞不清楚来源的,比如罗姆人(也称吉普赛人、冈茨人、波西米亚人)、马扎尔人(匈牙利人)、芬兰人、罗马尼亚人。罗马尼亚人跟罗马人是同时的。近代工业化从哪里起步呢?主要是南北欧,政治上我们又把南北欧合在一起称作西欧。东欧在这方面没有什么贡献。 讲这些什么意思呢?主要是为了解释美国文化的特性。它是北欧文化当中的海洋分支,盎格鲁-撒克逊这一支。它的文化基因跟它南边的邻国是不一样的。那边是南欧文化中的伊比利亚半岛这支。其实南北美洲都是欧洲人移民过去的,时间上就差半个世纪,但发展路径非常不同。北美应该讲比较成功;南美,坦率讲,屡战屡败,给近代世界做的贡献就是提供各种各样的教训。19世纪初他跟美国比工业化,败了;19世纪末跟德国、日本这些后来者竞争,又败了;二战后跟四小龙比,又败了;到现在跟中国比,又败了。所以也不要迷信欧洲,欧洲真正干得出色的主要就盎格鲁-撒克逊这么一小支。美国很幸运,移植的是比较成功的这一支。 如果以年为期,从地理大发现前后算起,在诸多民族里面,盎格鲁-撒克逊是最成功的。它先是用强盗手段把领先的两家打下去,一个是西班牙,一个是荷兰。它跟陆上国家竞争。跟高卢人打了年,英法战争它赢了。一战二战跟日耳曼人打,又赢了。冷战跟斯拉夫人打,也赢了。冷战后期插入一个小小的挑战者日本。中国呢,是它面对的一个新对手,谁输谁赢还不知道。 人物周刊:粗略地说这年的主线是盎格鲁-撒克逊和其他种族间的争斗? 2金灿荣:非常粗略,把竞争世界主导权作为主线来看的话,应该说它是最成功的。再回过头来看美国,它有些基本的性格,可以从文化角度解释。一个呢,它是个海洋民族,所以它的扩张性是非常强的。美国历史上始终有一个概念叫“新边疆”。美国历史学界有一个边疆学派,就是说美国历史就是不断扩展边疆的历史。地上边疆没了它就搞太空,“新边疆”。年美国实现了登月,肯尼迪提出登月计划时就说我为什么要搞登月?是为了“新边疆”。后来搞英特网也说是“新边疆”,来了一个虚拟世界的边疆。它是海洋民族的性格,到处跑,不断追逐鱼群。这种边疆意识导致美国的扩张性非常强。 第二个就是它商业性质比较强。最早去这个国家的人绝大部分是经济移民,今天去美国绝大部分也是经济移民。这导致这个民族商业精神非常强,因此也就比较现实主义,由商业利益驱动的现实主义。 第三个是理想主义。最早去13州的是经济移民。但年有一支比较怪,是清教徒,它受英国国教的压迫,为了追求宗教自由去了波斯顿,坐的五月花号。这一支是美国总在鼓吹的,因为这支比较道德、体面。其实你要知道它有13个兄弟姐妹,12个都是地痞流氓妓女,混不下去的。但人都喜欢神话自己道德的那一面。美国历史书强调它的立国精神来自这一支:我们是为宗教自由来的。在路上已经定了一个《五月花号公约》,集体领导、共和制、保障宗教自由。但你别忘了这只是1/13。不过这一支后来影响非常大也是事实,确实使他的理想主义成分比其他国家高一点。 人物周刊:既有现实主义,又有理想主义,不是很容易冲突吗? 3金灿荣:经常冲突。可以说,正常情况下都是现实主义占上风,当巨大的利益和原则发生冲突,美国人会放弃原则。美国佬从来不喜欢书呆子,教条主义在美国历史中早就被淘汰掉了。 美国还有个特点,就是因为他工业化非常成功,现代科技又很大程度上产生于这一支文明,它非常自信。美国人的爱国主义与众不同。一般的爱国主义都是发掘悲情,激发国民的团结:如果不团结,我们就要被灭亡了,民族主义就这么来的。美国民族主义是从自信来的,我盎格鲁-撒克逊种族、我美国是特殊的民族、特殊的国家、上帝的特殊选民。它的民族主义是自信的民族主义而不是悲情的民族主义。它很自信,又有使命感,所以总体上是扩张的。它有两面性格,一面是扩张主义一面是孤立主义。这两者有个共同的基础是道德优越感。当它需要扩张时,它基于道德优越感说,我这种生活方式太好了,我要不推广对不起上帝,所以你们必须学我。等到需要歇一歇了,道德优越感又出来了:外面的世界太肮脏了,不跟你们玩,我进一步搞好自己。它的道德优越感有时为扩张辩护有时为孤立辩护。 人物周刊:基辛格的《大外交》提出,冷战后世界会向多极格局发展,中国、印度、日本、欧洲等,都可能参与承担责任。天生有优越感的美国政府和美国普通民众,对这样的观点接受度如何? 4金灿荣:基辛格这样的还有几个,布热津斯基也差不多,说美国以后比较好的位置,就是一群领导者分担责任,但美国是班长。这是美国恰当的位置,你要做家长全管,那就不行了,别人受不了,自己也太累。这是他们头脑清醒的战略家提出的,我觉得比较符合美国利益,也比较符合世界现实。但这在美国是比较例外的声音,正确的例外。 人物周刊:在您看来,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依据吗? 5金灿荣:有依据。现在学界对冷战后世界有很多两分法,比如民主和专制、发达和落后,好像都太简单化了,中间有很多灰色过渡地带被抹得没有了,而且容易有争议。我现在用的是“四个主义”来分析。第一个就是文明主义,主要就表现在美国和伊斯兰世界。文明类型早就存在了,但当某一个人或一群人想用这个事实达到某种政治目的,就变成一种文明主义。亨廷顿、本?拉登,都在起这个作用。亨廷顿是在告诫西方人,说未来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之间,西方是一个整体,现在开始,德国人、法国人,你要忘掉你的身份,团结在以白宫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。它是这么个逻辑。本?拉登也一样,说我们生活这么糟就是西方欺负我们。现在开始,你要忘记你的埃及人、伊拉克人身份,心向我这个核心。他们的目标一样,就是要把一个长久存在的社会现象引导向某种政治目的。这就是文明主义,主要存在于伊斯兰和美国。 第二个叫地区主义。比如欧盟进一步联合、非洲国家统一组织变成非盟。中国也试图做一点,上海合作组织、中国东盟十加一,等等。这在各个地区都得发生,大家都觉得,在全球竞争的时代,光凭我一家不行,我拉上几个兄弟一块儿干好一点。 第三个是民族主义。它在冷战时期其实是被压制了,冷战后又都起来了。现在俄罗斯、美国、中国、日本、韩国民族主义都很强。韩国是最强的,一定要买国货。欧洲因为联合稍微弱一点。 第四个是部落主义,主要在非洲。非洲在民族独立后有过一个西方概念中的现代国家体系。可是几十年下来它那个体系不为人民服务,光为自己服务。所以政府信誉很差,非洲老百姓越来越依赖自己的传统部落。利比亚就在发生这个事,谁能争取到更多部落谁就是赢家——社会又回到部落状态了,所以叫部落主义。中亚、阿拉伯有些国家也有一点这个劲儿,但以非洲为代表。 提出这四个主义并不是一种主张,不是我偏好什么,它就是客观描述,我觉得透过这四个主义,冷战后各国的图景基本上就看清楚了。但它只是描述目前的格局,以后走向何方谁都不知道。 人物周刊:亨廷顿还写过一本书叫《谁是美国人》。 6金灿荣:《WhoAreWe》,我们是谁。那是另外一个问题,种族关系,以后美国最大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。实际上美国正在从民族熔炉走向民族的马赛克。过去美国人是很自信的,说我不管吸收多少外来民,最终他们都会成为接受美国价值的美国人。 《WhoAreWe》提出种族关系这个问题说明它的主流精英不自信了。这本书充满了忧虑,特别是对墨西哥裔美国人。这帮老兄是这样:在美国打工,地位很低,工作9个月,赚了很多钱——这个多只是相对于他们老家很多,然后还有3个月回家乡消费,做人上人,特爽。他虽然在你这里赚钱,却觉得他不是美国人。那本书开头讲有一年世界杯争出线权的是墨西哥和美国,比赛在洛杉矶举行,里面坐的很多都是墨西哥裔美国人,很显然那里成了墨西哥队主场。对球这个玩意儿的情感是自然流露的最朴素的。这使亨廷顿非常担心。这是个大问题,能不能解决不知道,我觉得是越来越困难。 人物周刊:现代化国家当中美国人信仰宗教的程度似乎特别深,这是为什么? 7金灿荣:美国很奇怪。一方面它是近代国家中第一个强调政教分离的,它在宪法里面明确写到不许设立国教。但另一方面,正因为它没有官方扶植的国教,人们信教是真信,特虔诚,所以美国人宗教感又是最强:信教的比例、捐款的比例、参加教会活动的比例都是极高的。很多美国人认为欧洲太世俗了,看不起欧洲人。很多欧洲人也看不起美国人:这帮傻帽还在信宗教! 人物周刊:我有个怀疑。对美国人来说原先上教堂是很好的组织方式,现在科技越来越发达,互联网、Facebook这样更方便更简捷的社交工具,会不会使美国传统的社会组织方式越来越弱化? 8金灿荣:很多人忧虑,这是对美国民主的一大挑战。原先美国民主的前提,是有一个很好的社区,大家定期到镇公所(townhall)去聊天、投票,镇子也不大,相互都熟,有很强烈的社区感——社区感的背后是他们所说的姐妹感、兄弟感。所以以前的政治参与是很实在的,就是说我喜欢他,就为他站台,为他去敲门拉选票。现在越来越变成这么一个游戏了:一家人坐在电视前,吃着土豆片,看着两个人唾沫横飞脸红脖子粗,号称是在为你说话。但你跟他没有私人关联,惟一的关联就是那人表演中的某句话触动你,你就给他块钱的支票,就是在签支票那一刻有了点关联,没有别的关联。 很多美国政治学家认为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对美国民主不利。我以前在美国大学的导师,本杰明?巴伯,他算是一个先驱,他就琢磨怎么在赛博空间(Cyberspace,指计算机、计算机网络中的虚拟现实)时代建立社区,甚至利用赛博空间来恢复社区活力。他认为这对美国民主能否健康保持下去很关键。 人物周刊:说到“普世价值”,我们常常会想到美国,在您看来,美国的哪些价值是普世的,谁都应该学、可以学? 9金灿荣:我觉得美国成功的经验有三方面,第一就是运气。 人物周刊:运气不算经验吧。 10金灿荣:但美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运气。所以现代德国之父俾斯麦到晚年就像祥林嫂似的,见了记者就抱怨,说上帝不公平,就喜欢三种人:第一白痴,第二酒鬼,第三美国人。 我随便讲几个数字:美国地理范围跟我们差不多大,人口是我们的四点五分之一,可是他的可耕地是我们的3倍,人均是十几倍。所以美国人就很潇洒,问好是“Howareyou”——“你好吗”,中国30年前问好都是“你吃了吗”。对中国人来讲吃饭永远是个问题,但对美国人从来就不是问题,他的问题是生产太多谷贱伤农。你想,吃是人最基本的体验,他的经验跟你不一样。这就是上帝的恩惠。 你再看水利,美国的四大水系特别棒:大西洋[13.55-1.67%股吧]水系、太平洋[8.90-1.33%股吧]水系、墨西哥湾水系,还有五大湖水系通到北冰洋。中国最主要的水系都是由西向东,来水时很集中,很难利用,平时呢没水,旱;一来来得特别多,涝。不来也是祸害来了也是祸害。美国基本风调雨顺。 总之美国确实受到上帝眷顾。美国经验的这一块,你要把它剥离出来。美国历史教科书是把它糅在里边写的。你要清醒,这部分就别学了,这叫运气。 第二就是学不来的部分。盎格鲁-撒克逊民族一些特有的价值观对他们是天然的,而你学不来。比如对政府的态度。他们都把政府定义为“必要的恶”,政府的本性是恶。而中国人把政府叫作什么?叫“天下之公器”。基本态度非常不一样。你要想让中国老百姓都跟盎格鲁-撒克逊民族一样,那中国人做不到的。所以中国的精英阶层在设计制度时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。 第三个部分是可以学的。比如它的创新精神、它的实用主义、它对失败的容忍、追求目标的时候不追求最好而追求次好,英文叫“secondbest”——这很了不得。因为人是贪婪的,就想着什么最好的都归我,但因为美国人的宗教观很强,他就认为最好只能是上帝的,只能追求差一点的次好。整个民族都接受次好概念。他们老说自己是英美式妥协,怎么来的?就是大家都接受次好。 另外思维上的经验主义也可以学,盎格鲁-撒克逊民族跟欧陆民族不一样,它是经验主义的,欧陆是唯理性主义,德国最厉害,比较容易走大的极端。英美经验主义的好处是它每推进一步都跟事实对照一下,你看起来不过瘾——特别是知识分子觉得比较肤浅,但人家不犯大错。这个是应该学的。 人物周刊:美国有推广自己价值观的冲动,但它有先发优势,生活水平、消费水平发展到了这个程度。别的国家学习它的价值观和制度恐怕也不能享有那种生活水平,而且地球也消耗不起。那我为什么一定要推崇、学习你这个制度? 11金灿荣:首先你要理解美国人。你要美国人不去吹这个不可能,他多少年都这样。就像单位里好吹牛那种人,你要他改这毛病他会憋出病来。所以首先要理解他这么做很正常。第二个是也要看到美国向外推广价值观有成有败。有些地方是成功的,比如它改造日本、德国就是成功的;有些地方不理想,美国模式搬到利比里亚,人过得跟鬼似的。海地也是,全部制度都是美国式的,不行。所以说它这个制度在它这里运作不错,移出去在少数地方也不错,但确实在很多地方效果不好。这是个事实。 人物周刊:效果不好,可能在美国人看来不是我的制度不好,是你学得不好。 12金灿荣:但这还是说明你医生不高明嘛。比如说治个人,治好两个,98个没治好。你说不是我医术不行是他们人不行,这逻辑上讲不通。再有就是你刚才讲的,美国希望把它的价值观推广出去但并不希望你分享它的利益。其他国家是反推的,有利益我才学你。美国说方式你得学我利益不能保证,这是自相矛盾的。你看美国的思路:一方面是美国特殊论,另一方面它的价值观又是普遍适用的,它有很多矛盾在里面。从我们来说首先理解美国,别太气愤——怎么老到我家来给我上课?它就这性格,否则它就不是美国了,你得习惯。至于接不接受,那是你自己的事。 金灿荣:假如你正坐在出租车上,刚好遇到一个不爱听交通台或评书的司机,正频繁调频。这时他调到了新闻频道,你听到一个男中音在发表他对利比亚局势的看法。司机的手还没从按钮上挪开,顺势又转到了国际频道。你又听到一个男中音在发表他对中美关系的看法。 忽然之间你意识到,这是同一个男中音! 这样的“怪事”真的有可能发生。第一次采访金灿荣的间隙,他就接受了两家电台的电话采访。“因为是录播,如果他们是同一个时段的节目,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” 用金灿荣的话说,他的时间被分割为7块:教学、研究、行政事务、政策讨论、受访、国际学术交流、中国太平洋学会学术工作部,“基本是被外面牵着跑”。他正尽量压缩后3块的比例。但我们第二次采访他那天,他早上去凤凰卫视录《震海听风录》,录完去上课,下午又接受复旦校友会的采访。很少穿西装打领带的他,那天的装束相当正式。不过采访结束后他就解了领带,换上布鞋,回归不羁。 他办公室里最打眼的,一是堆积如山的书刊杂志,一是角落的自行车。书刊杂志没时间看又不舍得扔,就像他读本科时买的那两三百本书也保存至今,“当然那是每本都读过,有的还读了好几遍”。至于自行车,那是他上下班的交通工具。 他刚去了一次美国。早先一年要去十几次,现在觉得那样有点傻,基本一年两次,因为美国社会比较稳定、透明,短时间内变化不大,保持一定的敏感度就行了。何况潮流也在变化,现在倒更多是美国人来中国了。平时要是不上课,每天总有两三拨人来找。“我们的变化大,他急于了解你就跑得勤。” 在大学教书,和年轻人保持交流,在必要的时候给他们一些指点,这样的生活,让金灿荣觉得愉悦。之前他在社科院美国所工作,几任领导都很优秀:李慎之、资中筠、王辑思……但研究所有点老气横秋。他都快50了,回去时所里的人都叫他“小金”。 采访中,他一再提到“幸运”这个词。“我们国家从相对贫穷走向相对富裕这个过程,我们是亲历者,每一步都感觉比以前好一些。我估计下一代就有一个问题,他们的起点比较高,幸福感反而会差一些,他没有上升的感觉,反倒容易有受挫感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挺幸运的,我是有点感恩的。” 在他的回忆里,整个童年、少年时代都“挺好的”。虽然那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工作,生活相当窘迫。祖父祖母死后,13岁的父亲就被老乡带出来打工,从此再没有回过家乡浙江。解放后他读夜大“扫盲”,3年就取得大专文凭,曾经作为武汉的两个代表之一参加年的全国第一届科技大会。他比较大男子主义,不许母亲去外面干活。三姐妹三兄弟和父母8口人挤在老旧的两居室,金灿荣和哥哥窝在阁楼,武汉的夏天多热啊,一家人居然其乐融融。 金灿荣上中学时,“文革”还没有结束,家里就有点担心,以后下乡你怎么办呢?结果高考恢复了。他原本是学理科,离高考还有10个月时转学文科。他所在的中学是理科重点,没有文科班,全校就他一个人学文科,只好转去一所普通中学。年高考他是文科武汉市第一湖北省第二,进复旦大学读国政系。几年后去北京,在社科院读硕士。 复旦那个班41人,毕业后的最高潮是有30人同时在国外学习。“一个班30个人跑到外面去,人家接受你,证明这个班很厉害啊!”后来这41个人各有各的发展,“都挺好的”,但留在学界的只剩下3个。 在复旦时金灿荣搞了不少活动,比如每周五组织班里的学术辩论,在社科院读研时他更一度成了风云人物。“那一届的研究生会人员结构很不合理,成员基本都是经济学部的,国际学部、法政学部都没有代表;会长又不得人心,公款请客。”他就领导同学把它推翻了,搞了个“民主试验田”,跟一位同学按“三权分立”原则合写了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会章程》。此外,因为伙食问题他还领导过两次食堂罢餐。 年他硕士毕业,留在了美国所,很快结婚生子,之后就开始了延续至今的美国研究。 年,金灿荣去哥伦比亚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,对美国有了直观的感受,心里有了点底,次年回国后开始评论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,并陆续引入文化视角。他觉得美国的确很成功,但很多美国经验在中国无效。年,他发表《美国的市民社会与政治民主》一文,认为美国的成功和市民社会大有关系。没有这个土壤,同样一个体系达不到美国那种成功度。而相对于西方,中国刚开始有中产阶级,量虽不小,却是以经济收入来定位的,还没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价值体系:事业顺利就从市场体系中借理论资源,混得不好掉到底层就变成了“愤青”,尚未形成社会学意义的“阶级”。 他觉得自由主义是现代人类的好选择,但这条路走起来未必顺畅;他当然也希望中国民主化,但对如何实现越来越不敢下断言。年代末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很多失败了:利比里亚和海地是国际社会的救济对象,菲律宾出口最多的是菲佣。他说自己渐渐成了“保守的自由主义者,反革命的革命派”。所以年之后,他开始在体制内“做事”。体制内本身也在改变,原来等级结构明晰。随着各方面的公共决策、外交决策越来越复杂,对相应的专业知识的需求也增加了,专业知识分子介入的内部讨论会越来越多。 二十多年来“小文章陆陆续续发了几百篇,没有满意的,也不系统”。金灿荣现在的心愿是未来10年内写两本书,“把自己对美国的理解和对中国的观察写出来”。另一个一直想做但还没有做成的,是用纯民间资源搭一个平台,对中国的战略、对外政策、中美关系,发出民间的声音。当然,也希望政府能听见。 让人颇有点意外的是,他反对政府把幸福感作为指标。“现在民间有这样的压力,政府有一部分人也是在打民粹牌。他要取悦民众,表面上接受了这个指标。其实许诺人民一定能够幸福这是任何政府都做不到的。所以我原则上反对政府把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作为执政目标。政府的指标应该是什么?努力为人们寻求幸福创造外部条件--这是政府应该做的。” 来源:南方人物周刊年7月 2 看完,如果喜欢,请积极传播,少量广告,还请大家支持!↓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nuojiyaa.com/njysh/6668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诺基亚首款北欧风格双曲面屏手机,一定能博
- 下一篇文章: 阿联酋正式免签,中国护照再升值免签落地